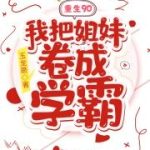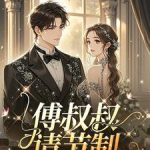第 129 章 尋春 (一)
第129章 尋春 (一)
在大明湖的南岸, 有一小亭依水而建,與歷下亭遙遙相望,檐飛入雲, 形制精美, 與河岸由一條狹長曲折的人工步道相連,名曰:天心水面亭。天心水面亭始于元代,為大學士李泂所建,亭名化用宋朝詩人邵雍《清夜吟》一詩中的“月到天心處,風來水面時”, 與春日的大明湖相得益彰。
此時,亭中有五位青年男女正倚欄而坐,凝望着煙波浩渺的大明湖,正是沈忘、柳七、程徹、易微和霍子謙。不知從什麽時候起, 只要歷城縣衙完結一段公案, 衆人便會到一風景秀麗之處淺酌小憩, 時間久了, 這樣極具儀式感的小聚便成了衆人心照不宣的默契。幾日前, 轟動整個濟南府的狐貍娶親一案真相大白, 歷城縣衙又回歸了往日的寧靜, 見春色尚好, 易微便提議泛舟大明湖,一賞湖畔春景, 衆人皆點頭稱是。
世人皆言濟南府有八景,分別是:錦屏春曉、趵突騰空、佛山賞菊、鵲華煙雨、彙波晚照、明湖泛舟、白雲雪霁、歷下秋風。這一說法源自何處已久不可考,但這濟南八景經過無數文人墨客、才子佳人的考驗傳頌至今, 可見其景色之美絕非浪得虛名,而其中這“明湖泛舟”就更是人間樂事。
五人于一晴好春日, 擇一輕舟小舫,泛舟湖上。小船飄飄蕩蕩,也沒有什麽刻意的目标,只是順水随風,自在來去。湖面水霧氤氲,滿目清涼,頭頂的日頭也不灼人,曬在身上舒适熨帖,似乎把連日來的困乏與疲憊一掃而光。易微帶了一口袋糕點,柳七攜了數卷醫書,霍子謙和程徹堆在船尾下棋,沈忘則獨自一人坐在船頭垂釣,小船之上歡聲笑語,天南地北聊得格外盡興。
沈忘的身邊擱着一個竹編的魚簍,裏面已經游着兩尾鯉魚。鯉魚秋日最肥,雖然現在時間尚早,可好在大明湖水草豐美,鯉魚也長得壯實,比別處的個頭兒都要大些,小小的魚簍已經被這兩尾魚填了個大半。
“大狐貍,你能不能快點啊,肚子都要餓扁了!”易微的嘴裏塞得鼓鼓囊囊,一疊聲地催促着。
正在看書的柳七将書卷微微下壓,透過書頁的邊沿看了一眼身邊翹着二郎腿的少女,無奈地笑了笑又把目光投向書中的字裏行間。沈忘則頭也不回地搶白道:“好飯不怕晚,就你這小狐貍心急。”
程徹也趕忙替好兄弟說話道:“微兒,你那口袋裏的糕點都吃光了?我這兒還有包果脯,你要不要先墊墊?”
“我就不,我就要吃魚!”
程徹光想着易微的肚子,卻忘了自己手底下的棋子,對面的霍子謙發出一聲志得意滿的歡呼:“哈!将軍!”
大意失荊州的程徹趕緊用手護住棋盤,埋怨道:“诶,老霍你這人,不算不算,我走神兒了!”
霍子謙哪裏肯依:“怎麽不算,程兄弟你早就敗局已定,前三步就走進死局了。”
“老霍你別诳我,有本事你讓我三步,咱們再來過!”
就在二人推搡吵鬧之際,一直老老實實坐在船頭釣魚的沈忘突然撐起身子,猛地向前紮去,一只手緊緊握住魚竿,另一只手在空中揮舞着保持着岌岌可危的平衡,整個人如風中楊柳擺蕩不斷。霍子謙背對着沈忘,并不知道沈忘此時的窘迫,可程徹卻是看了個滿眼,吓得一個箭步沖到船頭,撈住了沈忘的腰。
“無憂,你小心着!再掉下去!”
沈忘卻無暇他顧,拼盡全力握緊魚竿,大叫道:“鯉魚!金尾鯉魚!別管我,管魚!”
這平日裏谪仙人般的沈縣令,在釣魚一事上卻有着孩童般的執拗,釣到了便擊掌稱快,沒釣到便哀嘆連連,倒是一點官架子也沒有,而濟南府幾個有名的“煙波釣客”都是歷城縣衙的座上賓。這一次,也不怨得沈忘這般莽撞,這金尾鯉魚的确是大明 湖有名的珍馐,也是“錦鯉三吃”最好的原料。
沈忘這一喊,霍子謙和易微也坐不住了,都齊齊撲到船頭幫忙,扯魚線的扯魚線,拿網兜的拿網兜,抓釣竿的抓釣竿,捧魚簍的捧魚簍,柳七眼見着四人登臺唱戲般在船頭忙活了一炷香的時間,這才把那罕見的金尾鯉魚釣了上來。
程徹只覺抓條魚比連打五套拳都累,坐在船舷上大喘着氣,手中還不忘抓着沈忘的衣服下擺,生怕這不省心的無憂兄弟一個踉跄栽進湖裏。易微和霍子謙則興致勃勃地盯着魚簍中的鯉魚看,口中吸溜有聲:“三條了三條了,可以開飯了吧?”
“對對,先把這金尾巴的吃了,剩下的可以再養養。”
沈忘志得意滿地長出一口氣,手臂一揮:“上岸,開飯!”
五人将小舟停靠在湖岸的碼頭邊,早就有酒家的小二在岸邊候着了,接過魚簍便一溜小跑着往酒樓的後廚去了,衆人則沿着人工的步道向天心湖面亭走去。
柳七陪衆人行至亭中,并不坐下,而是拱手道:“諸位,我先失陪了,适才泛舟之時,我看見北岸有一城隍廟,我想先去上柱香。”
易微也是個坐不住的,聽說柳七要去城隍廟,也一疊聲地要跟着去。
“微兒,你不才說餓了嗎?”程徹問道。
“啧,坐着等也是餓,陪柳姐姐上香也是餓,還不如陪柳姐姐呢!”易微翻了個白眼兒,跟在柳七的身後屁颠屁颠地跑遠了。
霍子謙心中詫怪,問道:“我倒是沒聽說柳姑娘還拜城隍,這不年不節的,怎麽還要去城隍廟上香呢?”
“是啊,阿姊平日裏不是最不信這種神神鬼鬼的嗎?”程徹也疑惑地撓了撓頭,轉頭看向已經行到岸邊的兩位少女的背影。
亭中的風有些大,沈忘将兩只手攏在袖中,任由湖風吹亂他黑如鴉羽的發,他的眸光靜靜地凝在湖中心的一點,又似乎望着某些遙遠的不可知的彼方,緩緩開口道:“子謙是江西吉安人,自是不知這濟南府城隍廟的來歷……”
建文帝元年,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,發兵南下。建文皇帝派大将李景隆征讨,李景隆兵敗,河北、山東各地城鎮搖搖欲墜,望風而逃。燕王朱棣一路凱歌,攻城掠地,卻在濟南府碰了個硬釘子,那便是時任山東參政的鐵铉。鐵铉名如其人,鐵骨铮铮,忠心耿耿,坐鎮濟南府,親自督戰,矢志固守,将濟南府守得如同鐵桶一般,朱棣圍堵了三個月,愣是沒有将濟南府攻下來。其後,鐵铉又與盛庸一道北伐燕軍,更是打得燕王朱棣丢盔棄甲,師老兵疲,差點兒全軍覆沒。
在一個鐵铉身上吃了無數虧的朱棣,終于在建文三年率軍繞過了山東南下,經靈壁、宿州,最後攻下了南京。而兵敗被俘的鐵铉被盛怒的朱棣割下了耳朵、鼻子,扔進了油鍋,死前仍大罵不絕。
鐵铉死了,可濟南府的百姓們還活着,他們感激鐵铉固守濟南之恩、為民請命之仁、不事二主之義,為鐵铉立了祠堂。然而,永樂皇帝可不會允許自己治下的臣民還心心念念着這位靖難忠臣,派人前來責問。濟南府的老百姓們卻異口同聲地說,自己只是拜城隍,不是拜鐵铉,責問之人無功而返。自此,鐵铉的祠堂就真的成了一座城隍廟,老百姓們嘴上說着拜城隍,其實心中拜得卻是那鐵骨铮铮的“鐵城隍”。
“所以,柳姑娘拜得是鐵铉!”霍子謙面露崇敬之色,壓低聲音道。
沈忘沒有回答,他輕輕擡起手,指向環湖而生的垂柳:“子謙,你知道這些柳樹叫什麽嗎?”
霍子謙搖了搖頭。
“它們叫鐵公柳,這麽多年過去了,它們依舊在替鐵铉守着濟南城。每年鐵公忌辰,都會有濟南府的百姓手持柳枝,種在湖畔,所以大明湖畔的柳樹一年比一年只多不少。嘴可以被堵住,神像可以被砸爛,生命可以被掠奪,可公道卻始終在人們心中。”
沈忘說完,長身而起,面上一掃憊懶之色,鄭而重之地向着大明湖的北岸遙遙一拜。程徹和霍子謙也緊随其後地站起身,拱手而拜。
沈忘不知道為何柳七對這幫靖難忠臣永遠耿耿于懷,無論是被誅十族的方孝孺,還是被油炸的鐵铉,無論是在嘉興畫舫中,還是在濟南府的城隍廟,柳七似乎總是隐隐地在祭奠着什麽,懷念着什麽,而她也從來沒有向他直言相告。
聰慧如沈忘,若他真的想要知道這背後隐藏的答案,也許并非難事。但既然柳七不說,他便鐵了心思不問,他篤信二人之間的默契與信任,當他能夠知道的那日,柳七定然會告訴他。在那一刻到來之前,柳七說她拜城隍那便是拜城隍,柳七說她敬忠良那便是敬忠良。
淺淡的笑容浮上唇角,沈忘略一振衣,又在亭中坐了下來,以手撐腮,凝望着柳七和易微消失的方向。用不了兩炷香的時間,她們便會回來了吧?
正這般想着,岸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,沈忘和程徹、霍子謙三人回頭去看,正是剛剛離開的小二,此時他手提一個精美的食盒,正快速地向亭中行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