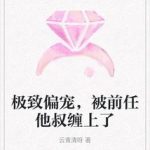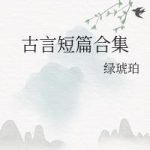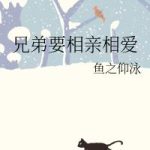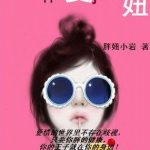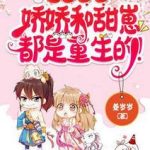第 227 章 兩百二十七章朕問你一個問題
所以,她剛才說了這麽多,都白說了?
還是說,方才的一切對話,都是她自個臆想出來的?皇上他老人家根本沒有與她說過話?
葉娴半張着嘴,腦子有些發懵地看向上方盛怒中的皇上。
“六弟妹不用這麽看着父皇,你一定行的。何況,現在時候不早了。”
幽王面含微笑地看向葉娴,語帶鼓勵,眸底的光芒卻幽深晦暗。他的話一出,立時提醒了皇上,令他點頭道,
“嗯,紫宸殿一衆愛卿還等着朕呢。再過半個時辰就該開宴了,朕不能掃了所有人的興。所以,你速上前與朕仔細看看。”
兩個跪地的官員似乎本是有異議不相信她的,但聽皇上這麽一說,忙又垂下頭,一副聽天由命的苦難表情。
仿佛她一上前,定會說出與他們不同的見解一般。
悄然掃了一眼雖蹙着眉卻無意阻止的文曜之,葉娴苦着臉暗嘆了一聲,不得不在殿中幾人驚異的目光注視下,來到死者身旁。
看來,她今兒是不賺這個經驗值都不行了?
有太監眼疾手快地走上前來,別開臉将布扯開,露出死者的面容來:雙目緊閉,面色白中泛青,面部皮膚微微突起,已現腫意。
初略一看,這婦人的死亡時間怕是至少在三天以上。好在現下天氣寒冷,氣溫偏低,屍體的腐爛很輕微。若是放在盛夏,只怕這大殿中根本沒法兒站人。
“怎麽樣?她是怎麽死的?”皇上皺眉看着這邊兒再次出聲,葉娴忙收起這些無關的想法,叫了太監将布徹底扯開,仔細查看死者的身體。
可是,死者的身體很完整,身上并無外傷。即便葉娴讓太監幫着将身體翻了個個兒,又看着宮女打着哆嗦用手将死者的衣衫解開徹底檢查了一遍,仍然沒有看出一丁點兒的外傷。
但有一個細節葉娴沒有錯過,就是死者的衣領處,有一條頂多手指寬的不是很明顯的污痕。
而正是這個細節,再結合上次那羅文病發時的情形,讓她瞬間猜到了死者的死因。
但,她要如何說,才能既讨得皇上的歡心,又不讓他對自己起疑?
蹲在死者身側的葉娴眉頭緊蹙,陷入了沉思。
“怎麽?還看不出來?”
皇上略顯平淡的聲音,帶出幾分他對這個結果的不喜。葉娴眉頭顫了顫,最終一咬牙站起身來,看向皇上:“依我……依臣媳看,此婦人年不過四旬,骨骼壯實,手臂粗壯,右手虎口與指腹間有厚繭,生前應常握重器……”
“父皇想聽的,并非這些。”幽王及時出口的話,令緊蹙眉頭的皇上贊賞地看了他一眼,“六弟妹還是不要再藏拙了吧?”
藏你妹啊,老娘又沒眼瞎,難道會看不出來?可他娘的,她敢随随便便把自己查驗到的結果說出來嗎?
葉娴在心裏暗吼了一聲,面上卻只得狀似拘謹為難地道:“可我胡亂翻看母親醫書,只學到了這些皮毛。實在看不出她是怎麽死的……”
“四皇兄太高看她了,”一直不曾言語的文曜之跟着淡淡地開了口,清冷雙眸掃了幽王一眼,“她不過一個獨自研讀母親所留醫書的醫不像醫的女子,豈能如張神探那般能幹?”
“不過,”在葉娴明顯感覺到皇上的眼神突地一冷時,文曜之像是未蔔先知一般,轉折的話語緊接着出口,看向她道,“她一向比本王更能觀察入微,雖不會驗屍,卻說不定能看出些有用的細節。”
所以,藏完拙之後,她還是要想辦法表現一下啊。否則,皇上看不到她的用處,如何信服他上回在殿中說的話,留她作甚?
“這婦人衣領間有一道淺淺的印痕,從紋路來看,像極了捆縛東西的麻繩留下的痕跡。”葉娴一面說着,又一面蹲下身子,将手伸向婦人的頸間,伸指在她頸間的盤扣處一捏,将一根極細的棕褐色毛狀物舉在手中,“這一根細絲,應該就是那麻繩與衣服摩擦時掉落的。”
至于這婦人就是被人隔着衣領用麻繩勒死這樣的結論,她是萬萬不能說出口的。
“六弟妹是想說這婦人是被勒死的嗎?”幽王緊緊凝視着葉娴,一字一頓地道。
那質疑的神情,讓人忍不住懷疑,方才那兩位官員說的死因,根本不是這個。
“是與不是,張大人定能看出來。”在葉娴沒想好怎麽回答之前,文曜之先一步幫她接過了幽王的話頭,“從這些細節看,可能性極大。”
“嗯嗯,臣媳能力有限,只能看出這麽點。”葉娴忙不疊地點頭,略帶羞愧地輕聲道。
但她心裏,卻百分之百确信自己的判斷沒有錯。因為,她意外賺到的5個經驗值,已經入帳了。
而此時的二二,正悠閑地飄蕩在她的眼前,品評着上座的皇上:“嗯,精神還不錯,暫時還沒有被他後宮的那三千佳麗徹底掏空。照這樣下去,再活個一、二十年,應該不成問題……”
你一個十幾歲的少年,就已經知道掏空是什麽意思了?
葉娴無語地瞪眼時,皇上忽然表情嚴肅地盯着她,在她心頭一跳時,忽地道,“那朕問你一個問題。被勒死的人,都會雙眼外凸、長舌外吐嗎?”
當然不是都這樣!
葉娴忍住了差點直接出口的話,假意低頭思考了一瞬,才緩緩搖頭:
“臣媳不知,世人都說,上吊或被勒死之人,死狀都是雙眼外突、舌頭外吐的。但據醫書上所載,人的舌頭雖然比我們看到的長很多,卻只有在壓到特殊位置時,才會外吐。所以臣媳有時覺得,世人所言,并不都對。照醫理來說,若不勒到那特殊位置,人的舌頭想必也是不會吐出來的。”
“是這樣的嗎?”皇上收回微微前傾的身體,重新坐正,在葉娴點頭回答時,他卻看向身後的屏風,笑道,“安神醫,除了張青,這已經是朕第二次看到有人贊同你的說法了。”